读完《呼兰河传》,对萧红惊为天人,真不愧为“30年代文学洛神”。不觉直感叹:天下的书真的是看不尽的;好作者太多了,好书太多了,时间太少了;以后还得多挤出点时间来看看这样的好书。
《呼兰河传》其实不太像一部小说,它情绪诗化,语言散文化,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。七个章节,勾勒了上世纪二十年代,北方小城浑成而斑斓的乡土画面,既有万物求生求荣的喜悦快意,也有生存的酸涩残酷,还有无知者的可怜可憎,以及弱者尤其是女性的凄凉悲歌。
在《呼兰河传》中的小团圆媳妇只因“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”,“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”,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一次又一次,直到被活活烫死……人们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扼杀别的不幸的人,在自己流血的同时,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,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。
萧红用她孩子气的笔触写下她回忆里的世界。她一字一句地叫嚷着,也像得了宝贝的孩子,兴奋得不时拿出宝贝来一枚一枚排出、一遍一遍细数。她不厌其烦地写“清早的叶子们”、“树的叶子们”;写“叶子上树了”、“花上树了”;写“大黄瓜,小黄瓜,瘦黄瓜、胖黄瓜,还有最小的小黄瓜纽儿”,这些文字,句句都带着满心的欢喜和珍惜。
萧红笔下是一派近乎稚气的天然,朝露晚霞,流云繁星,蝴蝶蚂蚱,花园菜地,还有世界上最疼爱她的祖父……那些无法复现的场景,永生难忘的欢乐,在她笔下越是绚丽明快,心里也就越是酸涩苦楚。她只是由着自己的直觉和心性诚恳地写,她的寂寞,她的悲哀,她的深情,还有她对生命的挚爱,所有这一切,都是她真实的自己。
萧红,对生命极为敏感,对生命的活力极为敏感。她是那么善于捕捉生命中的亮色,那么善于从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发现那跳荡着的生命力。对故乡充满童真的描述,是令人心醉的,也是让人心中充满温暖的。但是,无论怎样轻松的笔调,却处处令人感到一种深悲哀,她自己也反复在说一句话——“我的家是荒凉的”。
萧红在她的作品中把对象拟人化,把世间一切都当作有血有肉至情至性的东西来写,字字句句都见出她的体贴、疼惜和深情:“花开了,就像花睡醒了似的。鸟飞了,就像鸟上天了似的。虫子叫了,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。一切都活了。都有无限的本领,要做什么,就做什么。要怎么样,就怎么样。都是自由的。”
萧红有一颗儿童的水晶心。“太阳一出来,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,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。”她的才华流露,似乎是随心所欲的成分居多,仿佛“春来发几枝”的天然、率性。她像个摘花的女孩子,东一朵,西一朵,玫瑰也采,倭瓜花也摘,似乎漫不经心,聚拢来却是鲜灵灵的一篮,正看侧看都赏心悦目。
聂绀弩对萧红说:“萧红,你是才女,如果去应武则天皇上的考试,究竟能考多高,很难说,总之,当在唐闺臣前后,决不会到和毕全贞靠近的。”“我是《红楼梦》里的人,是那个痴丫头香菱。”香菱命苦,她也命苦。香菱生涯坎坷,却深具灵性,萧红更是有着惊世才华。萧红说:“我要飞,但同时觉得……我会掉下来。”
跟张爱玲比,萧红一生更加不幸,但是她的文字相对来说更健康,更温暖,更悲悯。她对贫贱的小人物,对一草一木,一鸡一犬,一山一石都充满了同情,她会花很大的篇幅,用很大的热情,用自己特别的割舍不掉的一种情怀去写。她写出一种对天地人间的关怀、悲悯,这种东西特别让人感动。
传说中有一种荆棘鸟,从离巢开始,便执着地寻找荆棘树。当它如愿以偿时,就把自己娇小的身体扎进一株最长、最尖的荆棘上,流着血和泪放声歌唱——那凄美动人、婉转如霞的歌声使人间所有的声音刹那间黯然失色!一曲终了,荆棘鸟终于气竭命陨,以身殉歌。
萧红就是这样一只荆棘鸟,她一生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,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。她用生命创造了美丽的永恒,而她以31岁年轻的生命离世,给人们留下一段悲怆的谜团。《呼兰河传》是一部回忆录,是一篇叙事诗,是一幅多彩的风土画,也是一串凄婉的歌谣,更是萧红这只荆棘鸟的生命绝唱。《呼兰河传》不朽,萧红不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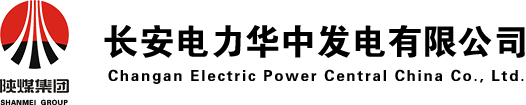


 友情链接:
友情链接: